作者:脑器官GC
2025年11月16日发表于第一会所
本站首发
字数:7,646
补充一下吕文德的背景:历史中应该是吕文焕,神雕侠侣改成吕文德了。
吕文焕守卫襄阳长达六年。弹尽粮绝后不得不出城投降。
此人肯定不会像一般小说中的那般无耻,也算是一个忠勇之人。
蒙古军从1268年开始围攻襄阳与樊城,采用持久围城 +水陆封锁。
阿术主持战役,史天泽、刘整协助。
刘整(原宋降将)帮蒙古军训练水军,造出巨舰。
蒙古军首次在中国使用回回炮(投石机),能掷火石破城墙。
结合长江舰队封锁运输线,切断襄阳粮道。
采用「合围 +断粮 +心理战」三法。
南宋中央(贾似道执政)一再拖延援兵。
夏贵、李庭芝等几次救援都被击退。
襄阳守军六年断粮断援,靠城中储粮苦撑。
夏贵本是一员猛将,老年贪生怕死,这次战役估计是个催化剂。
刘整是个关键人物,所以本书给他留了不少线索。
---------------
第七十四章:星星之火和无边黑暗
次日破晓,襄阳北门大开。忽必烈一袭玄色胡服,腰悬弯刀,胯下枣红马嘶
风欲踏。伯颜、阿术各领两百轻骑,玄冥真人一袭灰袍,负手立于马侧,寒气隐
隐。
启程前,玄冥真人对一名中年文士道:「慕容杰,我留一百多『金雕探子』
与武林好手交由你统领,你就暂且镇守襄阳,务必掘地三尺,擒杨过与小龙女。
此二人武功高强,不可单独为战,一定要以多取胜!我护大汗回大都后,不日就
会返襄阳,不要轻举妄动!」
慕容杰乃姑苏慕容后裔,以武为痴,博采众家之长,推引出「以彼之道,还
施彼身」的功夫,这些年他还琢磨一套点穴神术,已练至巅峰造极,是玄冥真人
手下有数的高手。他听罢抱拳,目露志在必得之意:「遵真人令!某虽不才,也
自问功夫不差,真人留下众多高手,当可一战!」
号角一响,铁蹄骤起,尘土漫天,忽必烈一行如黑云压城,瞬息没于北去官
道。
华筝静静站立,目送着对她有着复杂感情的这个北方霸主——她的亲侄——
离去。她对身侧的阳破天道:「你且安排一下在襄阳一带的传教事宜,大汗轻车
简行,我们也不能在此耽误太多时间,三日后返回大都。」
暮色沉沉,襄阳城西一隅的偏院里,枯叶在风中打着旋儿,像一群无家可归
的幽魂。
吕文德独坐廊下,膝上摊着一摞刚交出的兵符簿册,铜印已不在腰间,取而
代之的是「后勤总督」的空头衔。太守府也交予了伯颜的侄子兀良,自己被安置
在这个小院,落魄不堪。
烛火摇曳,映得他颧骨高耸,双眼深陷,活像一具被抽干血肉的躯壳。
他指尖死死摩挲着那枚旧铜印——那是襄阳守将的印信,曾是他荣耀与责任
所系,如今却成了捧在手心的滚烫废铁。
伯颜昨日亲临,笑容温煦如春风,言辞雅致似仕绅,只一句「大汗体恤吕卿
劳苦,军务暂交兀良」,便如温水煮蛙,将他二十年血汗铸就的兵权,连根拔起。
兀良,伯颜的侄子,二十出头,面嫩得像没长开的羊羔,却已趾高气扬地接管了
城防。这小子更拜了慕容杰为师,两人沆瀣一气。
吕文德亲眼看见那小子在校场指手画脚,蒙古骑兵对他毕恭毕敬,而曾经追
随他的汉人老兵却低头不敢语,眼神中满是死寂。
他心如刀绞,沸腾的血液里只循环着四个字:兔死狗烹!
他若不降,襄阳或许成为一片焦土,但至少死得其所,是南宋的忠魂;如今
苟活,却卑微得像大元的一条摇尾乞怜的走狗。
悔意如淬毒的蛇,一寸寸啃噬着他的心脏。他想起郭靖最后的身影——城门
洞开,郭靖手握长枪,独立于血泊之中。蒙古兵蜂拥而入,他却不退半步,回枪
自刎,血溅青砖。
那一幕,成了他脑中拔不掉的血色钉子,时时刻刻提醒他自己的背叛。
若我当时不开城,襄阳是否能多守几日?
若我与他并肩,是否也能死得轰轰烈烈?
他猛地摇头,将那念头甩开。不,不。城中三十万军民,粮尽援绝,守下去
不过是陪葬。他吕文德保住了他们的命,保住了自己的妻儿老小,这有什么错?
可为何夜夜梦回,郭靖那双澄澈的眼睛总在黑暗中盯着他,目光如刀,解剖
着他所有的借口。
吱呀——
院门被推开,寒风卷着枯叶扑进来。一名蒙古侍卫踏入,高声道:「华筝殿
下在议事厅召见吕将军,即刻前往!」
吕文德心头一震,一股莫名的寒意从脊椎升起。他匆忙起身,整了整凌乱的
衣冠,随侍卫而去。夜色中,他被带至原太守府侧的议事厅,如今已经换成大元
议事行辕,守卫森严。
厅内,华筝一袭素色胡装,风帽已卸,端坐主位。她身后屏风绘草原烈马,
只露一双清亮眼眸,却比满堂卫士更添威压。她抬手示意,侍卫退下,厅门轻阖。
「吕文德。」她声音清冷,如冰泉击石,不带一丝温度,「金刀驸马的守城
往事,与我说说。」
吕文德闻言,双膝一软,扑通跪倒,冷汗如浆,顺着鬓角滚落,浸湿了衣领。
他声音发抖,断断续续:「郭……郭大侠守襄阳十年,城中粮尽,他亲自扛粮上
墙;箭尽,他以身挡箭。城门口那日,他一夫当关,杀敌上百……鞑……大元勇
士围他如铁桶。他……他不愿降,回枪自尽。」
他本想说「鞑子」,话到嘴边,却猛地记起自己如今也是「大元之臣」,一
个寒噤,连忙改口。说到最后,他几乎语不成声,汗水滴落在青砖上,洇出深色
的痕迹。这不仅是郭靖的死,更是他自己良知的宣判。
华筝轻声道,听不出情绪:「说详细点,从他到襄阳开始说起。」
「…………」,「…………」,「…………」
吕文德不敢怠慢,从郭靖和他结识,两人一起并肩作战、笑傲沙场、共守襄
阳,度过了十年的时光。起初还略有些含糊,说着说着,往日袍泽之情涌上心头,
他忘了眼前人的身份,也忘了自己的降将身份,竟有些激动起来,眼圈发红。
华筝静静听着,见他真情流露,自己的眼圈也微微红润。她看向厅外城头猎
猎的「元」字大旗,声音悠悠,带着一丝飘忽的怅惘:「金刀驸马在襄阳多年,
可过得快乐?」
吕文德不敢抬头,犹豫了半晌,终于大着胆子回答,语气中却带着一丝被触
及灵魂的坚定:「郭大侠死前说,他常驻襄阳,死得其所。和末将守城十年,虽
颇劳乏,但……但他乐在其中。末将曾受人之托将他调走,他未曾离去。」说出
这句话时,他仿佛又变回了那个与郭靖并肩的宋将,而非此刻的阶下囚。
华筝目光一闪,沉默片刻,话锋陡然转厉:「你偷偷开城,放我大元兵入,
间接害他身亡。吕文德,你可后悔?」
这个问题如一道惊雷,在吕文德脑中炸开。他额头重重抵地,汗水混着泪水,
喉咙里发出呜咽般的低吼。他想辩解,想怒吼,想痛哭,却一个字也挤不出来。
悔意、恐惧、羞耻、愤怒,四把尖刀同时剜着他的心。
华筝俯视着他,声音低沉而极具穿透力:「说实话!」
吕文德猛地抬头,又迅速俯首,声音嘶哑得如同破锣:「不……不后悔…
…大宋腐朽不堪,赵禥昏庸无道!朝廷奸佞横行!我保不住襄阳……但我……我
保住了百姓……」这番话说出口,他自己都觉得苍白无力。
华筝发出一声几不可闻的冷笑,目光如刀:「大宋腐朽,那我大元如何?」
吕文德脸色煞白如纸,嘴唇颤抖,汗水滴落得更快。他想起伯颜那笑里藏刀
的脸,兀良那颐指气使的姿态,蒙古兵挥向平民的屠刀,城中汉人那低眉顺眼的
死寂眼神……他张了张嘴,喉咙里滚动着「残暴」二字,却终于被恐惧扼住,失
去了所有勇气:
「臣乃新降之人,不敢妄议大元……」
华筝起身,缓步近前,声音如冰刃划过他的耳畔:「我大元的毛病,我自知
晓。金刀驸马若无挂念,怎会弃草原驸马之荣,千里来守这襄阳?儒家汉制,懦
弱如羔羊,待宰而已;长生天的勇士,杀戮成性,贪婪如豺狼。可这世间,不该
只有羔羊与豺狼,人,也不该如此。」
她从袖中取出一本薄薄的经卷,封皮暗红,隐隐有火焰纹路,递到吕文德颤
抖的手中:「这《明尊经》,你若痛苦迷茫,便翻来读读。或有明路。」
吕文德捧着书,双手发颤,指节因用力而泛白。他抬头看向华筝,眼中满是
惊惶、困惑,还有一丝被看穿后的绝望。
华筝的目光深邃如夜空中的星火,声音低得像是贴着他的耳朵在呼吸:「汉
水之畔、襄阳和鄂州的汉人,三十几万生灵,不再是羔羊,也无需再向豺狼乞活。
他们需有人为他们指一条路。你若愿意,有人自会引你——引他们。」
她转身拍了拍手,不再多言,衣袂掠过烛火,影影绰绰。阳破天推门而入,
恭送吕文德离去。夜风卷着他失魂落魄的背影,消失在长廊尽头。
吕文德回到偏院,像一尊石像跪坐灯下,久久无语。烛火跳动,映得那经卷
上的火焰纹路如活物般蠕动。他低头,用颤抖的手翻开书页,第一行字跃入眼帘:
「明神在上,照我前路。」
他指尖一颤,一滴滚烫的泪水砸在纸上,洇开一团浓重的墨痕。窗外夜色如
墨,风声如泣,他捧着这本薄薄的书,像捧着天下唯一的火种,胸中剧烈起伏,
久久不能平静。
次日清晨,襄阳北门再度大开。华筝一袭银狐裘袍,腰束玉带,胯下白马如
雪。她身后百余骑护卫,旌旗猎猎,阳破天紧随其侧。
她回望城头一眼,目光掠过那面「元」字大旗,终究未发一言。马蹄踏碎晨
霜,一行人渐行渐远,尘土掩去了背影。
吕文德立于城门洞下,双手笼在袖中,怔怔望着那抹白影没入官道尽头。风
卷残旗,吹得他鬓发微乱,心头却空落落的,像被挖去一块。华筝昨夜那句「有
人自会引你」,犹在耳畔回响,可他仍不知该信几分,又该怕几分。
「吕大人。」身后忽响起生硬的汉音,带着年轻人的傲慢。
吕文德回身,只见兀良大步而来。少年将军一身玄色软甲,腰悬短刀,嘴角
噙着惯常的轻蔑。两名亲兵提着灯笼,随行的竟还有慕容杰——灰袍飘飘,手按
腰间软剑,神情淡漠。
「地牢里的宋军降将、丐帮余孽,一个个嘴硬得很。」兀良冷笑道,「大汗
有令,降者免死,不降者……哼。吕大人,你是旧日襄阳守将,总该陪我走一趟,
省得他们说我们蒙古人不懂『仁义』。」
吕文德喉头一紧,只得拱手:「末将遵命。」
地牢位于太守府后,阴湿逼人。火把照亮铁栅,映出一张张憔悴面孔:有断
臂老卒,有血迹斑斑的丐帮弟子,还有几位昔日同僚——他们衣衫褴褛,却仍挺
直脊梁,目光如炬。
兀良踱步而行,靴跟敲得石板咚咚作响。「都不愿降?」他嗤笑,「杀了便
是,省得浪费粮食。」
吕文德心头一颤,忙道:「将军,这些人……好歹是本地子弟,杀之可惜。
或可再劝——」
「劝?」兀良斜睨他,「吕大人,你心软得紧。来人,一个个压回去,不肯
招供情报的,午时斩首!」
亲兵应诺,拖拽声、铁链声顿时大作。牢中有人破口大骂「鞑子」,有人低
声啜泣。吕文德双拳紧握,指甲掐进掌心,却终究不敢再言。
兀良忽然停步,眯眼问:「那金刀驸马的徒弟武敦儒和他妻子在哪?」
吕文德咽了口唾沫:「地牢狭窄,不够安置,已……已囚在隔间。」
兀良挑眉,眼中闪过一丝玩味:「哦?你对敌人倒体贴。带上来。」
片刻后,武敦儒与耶律燕被推入临时审讯的偏厅。两人皆以铁链锁肩,衣衫
虽破,却难掩昔日风采。
武敦儒眉宇间犹带郭氏弟子的刚正,耶律燕则高挑修长,比武敦儒还高出一
头,腰肢丰盈,胸脯起伏,即便狼狈,仍有种胡族女儿的英气。
兀良的目光在耶律燕身上定住,少年喉结微动。那双眼睛亮得吓人,像狼盯
上了羊羔。
他平日仗着伯颜是自己叔父,最喜掳掠良家,调教倔强女子,却第一次看到
如此高挑英武的身子,这种高大与丰满的极致结合,让他食指大动,心底涌起一
股阴暗而狰狞的征服欲——一种小马拉大车的征服欲,他要这高挑丰满的侠女,
跪在自己脚下,哭着求饶,求他操弄,甘为玩物。
这欲望的根源,要追溯到他年幼时某个午后。那年他不过十岁,草原上的风
正烈,吹得毡帐外的马匹嘶鸣不休。他本是偷偷溜回叔父伯颜的王帐,想讨些糖
果解馋,却在门帘缝隙处僵住身子,像被无形的铁链锁住了脚踝。
帐内羊毛地毯上,叔父伯颜那魁梧如熊的身躯正压着一个女人——不,不是
一般的女人,是他的母亲。
平日里高傲得像草原上最桀骜的母狼,此刻却赤条条地跪伏在地毯上,像一
条发情的母狗般撅起那对雪白丰满的肥臀。
高高翘起的臀丘圆润得惊人,臀肉厚实而弹性十足,随着伯颜的动作剧烈颤
动,荡起层层肉浪。母亲的腰肢本就修长有力,却在叔父的粗手中被死死掐住,
迫使她上身贴地,脸颊摩擦着粗糙的地毯,乌黑的长发散乱如瀑,遮不住那张平
日威严如今却扭曲得近乎淫荡的脸庞。
伯颜跪在她身后,裤子褪到膝弯,那根蒙古汉子特有的粗长阳具——青筋暴
绽、龟头紫红如拳——正一下下凶狠地捅入母亲的蜜穴。
插入的瞬间,母亲的臀肉被撞得向两边分开,露出那粉嫩的菊蕾和被撑得变
形、泛着水光的肉唇。阳具拔出时,带出一缕缕晶莹的淫液,拉成丝线,滴落在
地毯上;再猛地顶入,龟头直撞花心,发出「啪啪」的湿响和肉体撞击的闷声。
母亲的那处神秘的地方,那是他出生他的地方,他就是从那个神秘的地方被
生养出来,这个神秘之处被他看的一清二楚,这也是他第一次知道蜜穴是什么,
长什么样。
童年想象中母亲的蜜穴本是紧窄的,却在叔父的抽插下被撑得红肿外翻,穴
口四周的嫩肉翻卷着,像是被征服的战场,沾满白浊的战浆。
「啊……伯颜……轻些……你这畜生……」母亲的声音本该是怒吼,却化作
断断续续的娇喘和呜咽。她试图挣扎,双手抓挠地毯,指甲抠出道道痕迹,可伯
颜只是大笑,一手揪住她的长发往后拽,迫使她仰起头,露出修长的脖颈;另一
手则重重拍在她臀丘上,留下五道红印,臀肉抖动得更剧烈。
「嫂嫂,叫大声些!我是不是比兄长插的你更爽!」伯颜低吼,腰杆如打桩
机般狂顶,每一下都顶到最深,阳具根部撞上母亲的臀缝,发出沉闷的「啪」声。
母亲的脸上,痛苦与快感交织成一种诡异的痴迷。她咬着唇,试图压抑,却
终究忍不住张开嘴,发出高亢的浪叫:「嗯……啊……要死了……伯颜……你比
他插的爽……」
她的身体背叛了意志,那对硕大的乳房垂吊在地毯上,随着撞击前后甩动,
乳头硬挺如樱桃,摩擦得地毯湿了一片。汗水从她高挑的脊背滑下,汇入臀沟,
再被阳具带出,混着淫液溅得到处都是。
她的臀部本是那么骄傲的弧线,如今却像献祭般高撅,迎接叔父一次次野蛮
的侵入,穴内层层褶皱被阳具碾平,又在拔出时贪婪地吮吸,仿佛舍不得那根征
服者的肉棒离开。
兀良躲在门帘后,小小的身子颤抖不止。他本该冲进去哭喊,可一种陌生的
热流从下腹升起,让他双腿发软。
那一刻,他看见母亲——那个能单手拎起羊羔、目光如刀的女人——在叔父
身下彻底崩塌,化作一滩春水。她的快乐不是伪装的,那种从骨子里涌出的颤栗、
那种从灵魂中对父亲的背叛,那被填满后的满足,让他这个偷窥的孩子第一次感
受到权力的真谛:征服高大的女人,让她们在自己胯下如狗般乞怜。
从那天起,这画面如魔咒般烙在他心底。母亲背叛父亲的影子成了他所有欲
望的模板:高挑、丰满、倔强,却最终屈服。
那些被他掳来的女子,他总试图重现那场景——让她们跪伏、撅臀、浪叫,
可她们要么太娇小,要么太顺从,从未真正触及他内心的空洞。
直到看见耶律燕。那女人身高近五尺八寸,骨架匀称,胸脯饱满得衣衫欲裂,
腰肢收紧,臀线圆润挺翘,带着胡族野性的力量感。她的影子与母亲重合得惊人:
同样高大,同样英武,同样有一股不屈的傲气。
兀良想象着将她按在地毯上,像叔父对待母亲那样,背叛了自己的夫君,撕
开她的衣衫,掰开她修长的双腿,看着那丰满的臀丘在自己阳具下颤抖、开花,
穴口被撑得红肿,淫液四溅。她会挣扎,会咒骂,可最终会像母亲一样,发出那
种混杂痛苦与痴迷的呻吟,彻底臣服。
这不是爱欲,而是扭曲的仇恨与自卑。他恨伯颜抢走了父亲的财产、母亲的
威严、培育过自己作为卵子的子宫,把自己生出来的通过的那条专属的阴道,却
又羡慕那征服的快感。
他要证明自己比叔父更强,通过耶律燕——这个比母亲更完美的猎物——来
填补童年的裂痕。让她哭泣、求饶、撅起屁股如狗般迎接他的阳具,那时,他才
能真正成为草原上的狼王,而不是伯颜脚下的影子。
伯颜对他颇为看重,他心下了然,但每次心里都隐隐作痛——莫非自己是伯
颜的种?而不是对他恩重如山的父亲!
武敦儒看他贪婪的、几乎要将妻子生吞活剥的目光,不由得怒骂:「鞑子小
儿,有种冲我来!」
兀良充耳不闻,缓步逼近耶律燕,比了比身高,自己的头才到她的双唇处。
这身高差非但没有让他退缩,反而更刺激了他的兽性。他忍不住伸手挑起她下颌。
耶律燕猛地一甩,力气奇大,险些挣开铁链。兀良却笑得更欢:「哟,野马劲儿。
放心,我不急。」
他手指下滑,隔着破损的衣襟,肆意抚过她饱满的胸脯,又探向那不堪一握
的纤腰与挺翘的臀线。耶律燕羞愤欲死,拼力挣扎,铁链哗啦作响,口中骂声不
绝。
那挣扎非但没有激起兀良的半分怜悯,反而让他脸上的笑容愈发狰狞,享受
着这猎物临死前的反扑。
兀良低笑,声音里满是病态的快感:「再动,我就剁了你夫君一根手指,如
何?」
耶律燕浑身一僵,泪水在眼眶打转,似断了线的珍珠,却终究垂下头,任那
只手继续亵玩。武敦儒目眦欲裂,嘶吼着扑来,却被亲兵死死按倒,脸颊在粗糙
的石地上摩擦,发出痛苦的闷哼。
吕文德再也看不下去,胸口仿佛被巨石堵住,他踏前一步,声音都走了调:
「将军!她……她是女流——」
「女流?」兀良终于将目光从耶律燕身上移开,转向他,眼珠一转,笑得阴
鸷如鸮,「吕大人,我可没用刑,也没强迫。我只是问话。」
他转向慕容杰,语气变得轻佻而理所当然,「慕容先生,你那点穴功夫,能
让这娘们儿使不出半分力气?」
慕容杰淡淡一笑,似对女色浑不在意,眼中只有对武学的痴迷:「自然。姑
苏慕容,点穴天下第一。七日内她就和常人无异。」话音未落,他指尖如电,连
点耶律燕数处大穴。耶律燕只觉四肢百骸瞬间一麻,一股酸软感席卷全身,顿时
软倒在地,再无半分内力,像一尊被抽去骨架的精美雕像。
兀良满意地拍手,俯身在耶律燕耳畔,用只有两人能听到的声音低语:「我
听吕大人的,不强迫你。但你若自己送上门来……可别怪我把你夫君的十根手指,
一根根喂狗。」他直起身,冲亲兵一摆手,「带走,好生『伺候』。」
吕文德又惊又怒:「华筝殿下已有懿旨,不得害他二人性命!」
兀良冷下脸色,一字一句道:「我可没说要她的命!我一没动刑,二没逼供,
只是单独问话。吕大人,你管得未免太宽——你如今,不过一介后勤都督!」
「后勤都督」四个字,像四根钢针,狠狠扎进吕文德的心里。他僵在原地,
眼睁睁看着耶律燕被两个亲兵像拖拽一件货物般拖走。她被拖走时,奋力回眸望
向夫君,那眼神,从绝望变成死寂,像一滩再也无法燃起的血。
「不——!」武敦儒发出野兽般的嘶吼,用尽浑身力气撞向铁栏,额头血流
如注,顺着他年轻而刚毅的脸庞蜿蜒而下,触目惊心。
慕容杰负手而立,目光只在耶律燕被点中的穴位处流连片刻,便已移开,仿
佛刚才只是完成了一次精准的解剖实验。
兀良则哼着草原上的小曲,嘴角勾起,脑中已浮现那高挑丰满的身躯在自己
身下颤抖、屈服的模样——他要慢慢折磨,慢慢调教,直至她心甘情愿,将他视
为主人,甘为性奴。
地牢火把噼啪作响,照得众人影子扭曲如鬼魅,在墙壁上疯狂舞动。吕文德
踉跄后退,胸口堵得发慌,仿佛肺里灌满了这地牢里腐烂的空气。他靠在冰冷的
墙壁上,指节无意识地死死抠着墙缝,指甲崩裂也浑然不觉。
他落寞地走出地牢,清晨的阳光刺眼,却没有半分暖意。他像一个游魂,回
到那方偏院,瘫倒在廊下。
这里,曾经是他府邸的一部分,如今却成了他的囚笼。世界变了,只是变得
太快,快得让他来不及死,只能苟活。
他闭上眼,武敦儒额头流下的血,和耶律燕那死寂的眼神,在他脑中反复交
替。那不是将士的死,那是羔羊在被豺狼分食前,最后的哀鸣。而他就是那个打
开羊圈的人。
悔恨、无力、屈辱……像无数只噬心之虫,啃得他千疮百孔。他猛地想起昨
夜华筝递来的那本经卷,颤抖着手从怀中掏出。
封皮暗红,火焰纹路在阳光下若隐若现,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又像一抹不灭
的星火。他翻开书页,那「明神在上,照我前路」八个字,仿佛带着一种奇异的
魔力。
「照我前路……」他喃喃自语,眼中一片迷茫,「我的路在哪?在这豺狼遍
地的地狱里,哪有路?」
他想把书扔掉,想撕碎这虚假的希望。可手指一接触到那温热的书页,却又
舍不得。这是他唯一的慰藉,也是他唯一的毒药。
2025年11月16日发表于第一会所
本站首发
字数:7,646
补充一下吕文德的背景:历史中应该是吕文焕,神雕侠侣改成吕文德了。
吕文焕守卫襄阳长达六年。弹尽粮绝后不得不出城投降。
此人肯定不会像一般小说中的那般无耻,也算是一个忠勇之人。
蒙古军从1268年开始围攻襄阳与樊城,采用持久围城 +水陆封锁。
阿术主持战役,史天泽、刘整协助。
刘整(原宋降将)帮蒙古军训练水军,造出巨舰。
蒙古军首次在中国使用回回炮(投石机),能掷火石破城墙。
结合长江舰队封锁运输线,切断襄阳粮道。
采用「合围 +断粮 +心理战」三法。
南宋中央(贾似道执政)一再拖延援兵。
夏贵、李庭芝等几次救援都被击退。
襄阳守军六年断粮断援,靠城中储粮苦撑。
夏贵本是一员猛将,老年贪生怕死,这次战役估计是个催化剂。
刘整是个关键人物,所以本书给他留了不少线索。
---------------
第七十四章:星星之火和无边黑暗
次日破晓,襄阳北门大开。忽必烈一袭玄色胡服,腰悬弯刀,胯下枣红马嘶
风欲踏。伯颜、阿术各领两百轻骑,玄冥真人一袭灰袍,负手立于马侧,寒气隐
隐。
启程前,玄冥真人对一名中年文士道:「慕容杰,我留一百多『金雕探子』
与武林好手交由你统领,你就暂且镇守襄阳,务必掘地三尺,擒杨过与小龙女。
此二人武功高强,不可单独为战,一定要以多取胜!我护大汗回大都后,不日就
会返襄阳,不要轻举妄动!」
慕容杰乃姑苏慕容后裔,以武为痴,博采众家之长,推引出「以彼之道,还
施彼身」的功夫,这些年他还琢磨一套点穴神术,已练至巅峰造极,是玄冥真人
手下有数的高手。他听罢抱拳,目露志在必得之意:「遵真人令!某虽不才,也
自问功夫不差,真人留下众多高手,当可一战!」
号角一响,铁蹄骤起,尘土漫天,忽必烈一行如黑云压城,瞬息没于北去官
道。
华筝静静站立,目送着对她有着复杂感情的这个北方霸主——她的亲侄——
离去。她对身侧的阳破天道:「你且安排一下在襄阳一带的传教事宜,大汗轻车
简行,我们也不能在此耽误太多时间,三日后返回大都。」
暮色沉沉,襄阳城西一隅的偏院里,枯叶在风中打着旋儿,像一群无家可归
的幽魂。
吕文德独坐廊下,膝上摊着一摞刚交出的兵符簿册,铜印已不在腰间,取而
代之的是「后勤总督」的空头衔。太守府也交予了伯颜的侄子兀良,自己被安置
在这个小院,落魄不堪。
烛火摇曳,映得他颧骨高耸,双眼深陷,活像一具被抽干血肉的躯壳。
他指尖死死摩挲着那枚旧铜印——那是襄阳守将的印信,曾是他荣耀与责任
所系,如今却成了捧在手心的滚烫废铁。
伯颜昨日亲临,笑容温煦如春风,言辞雅致似仕绅,只一句「大汗体恤吕卿
劳苦,军务暂交兀良」,便如温水煮蛙,将他二十年血汗铸就的兵权,连根拔起。
兀良,伯颜的侄子,二十出头,面嫩得像没长开的羊羔,却已趾高气扬地接管了
城防。这小子更拜了慕容杰为师,两人沆瀣一气。
吕文德亲眼看见那小子在校场指手画脚,蒙古骑兵对他毕恭毕敬,而曾经追
随他的汉人老兵却低头不敢语,眼神中满是死寂。
他心如刀绞,沸腾的血液里只循环着四个字:兔死狗烹!
他若不降,襄阳或许成为一片焦土,但至少死得其所,是南宋的忠魂;如今
苟活,却卑微得像大元的一条摇尾乞怜的走狗。
悔意如淬毒的蛇,一寸寸啃噬着他的心脏。他想起郭靖最后的身影——城门
洞开,郭靖手握长枪,独立于血泊之中。蒙古兵蜂拥而入,他却不退半步,回枪
自刎,血溅青砖。
那一幕,成了他脑中拔不掉的血色钉子,时时刻刻提醒他自己的背叛。
若我当时不开城,襄阳是否能多守几日?
若我与他并肩,是否也能死得轰轰烈烈?
他猛地摇头,将那念头甩开。不,不。城中三十万军民,粮尽援绝,守下去
不过是陪葬。他吕文德保住了他们的命,保住了自己的妻儿老小,这有什么错?
可为何夜夜梦回,郭靖那双澄澈的眼睛总在黑暗中盯着他,目光如刀,解剖
着他所有的借口。
吱呀——
院门被推开,寒风卷着枯叶扑进来。一名蒙古侍卫踏入,高声道:「华筝殿
下在议事厅召见吕将军,即刻前往!」
吕文德心头一震,一股莫名的寒意从脊椎升起。他匆忙起身,整了整凌乱的
衣冠,随侍卫而去。夜色中,他被带至原太守府侧的议事厅,如今已经换成大元
议事行辕,守卫森严。
厅内,华筝一袭素色胡装,风帽已卸,端坐主位。她身后屏风绘草原烈马,
只露一双清亮眼眸,却比满堂卫士更添威压。她抬手示意,侍卫退下,厅门轻阖。
「吕文德。」她声音清冷,如冰泉击石,不带一丝温度,「金刀驸马的守城
往事,与我说说。」
吕文德闻言,双膝一软,扑通跪倒,冷汗如浆,顺着鬓角滚落,浸湿了衣领。
他声音发抖,断断续续:「郭……郭大侠守襄阳十年,城中粮尽,他亲自扛粮上
墙;箭尽,他以身挡箭。城门口那日,他一夫当关,杀敌上百……鞑……大元勇
士围他如铁桶。他……他不愿降,回枪自尽。」
他本想说「鞑子」,话到嘴边,却猛地记起自己如今也是「大元之臣」,一
个寒噤,连忙改口。说到最后,他几乎语不成声,汗水滴落在青砖上,洇出深色
的痕迹。这不仅是郭靖的死,更是他自己良知的宣判。
华筝轻声道,听不出情绪:「说详细点,从他到襄阳开始说起。」
「…………」,「…………」,「…………」
吕文德不敢怠慢,从郭靖和他结识,两人一起并肩作战、笑傲沙场、共守襄
阳,度过了十年的时光。起初还略有些含糊,说着说着,往日袍泽之情涌上心头,
他忘了眼前人的身份,也忘了自己的降将身份,竟有些激动起来,眼圈发红。
华筝静静听着,见他真情流露,自己的眼圈也微微红润。她看向厅外城头猎
猎的「元」字大旗,声音悠悠,带着一丝飘忽的怅惘:「金刀驸马在襄阳多年,
可过得快乐?」
吕文德不敢抬头,犹豫了半晌,终于大着胆子回答,语气中却带着一丝被触
及灵魂的坚定:「郭大侠死前说,他常驻襄阳,死得其所。和末将守城十年,虽
颇劳乏,但……但他乐在其中。末将曾受人之托将他调走,他未曾离去。」说出
这句话时,他仿佛又变回了那个与郭靖并肩的宋将,而非此刻的阶下囚。
华筝目光一闪,沉默片刻,话锋陡然转厉:「你偷偷开城,放我大元兵入,
间接害他身亡。吕文德,你可后悔?」
这个问题如一道惊雷,在吕文德脑中炸开。他额头重重抵地,汗水混着泪水,
喉咙里发出呜咽般的低吼。他想辩解,想怒吼,想痛哭,却一个字也挤不出来。
悔意、恐惧、羞耻、愤怒,四把尖刀同时剜着他的心。
华筝俯视着他,声音低沉而极具穿透力:「说实话!」
吕文德猛地抬头,又迅速俯首,声音嘶哑得如同破锣:「不……不后悔…
…大宋腐朽不堪,赵禥昏庸无道!朝廷奸佞横行!我保不住襄阳……但我……我
保住了百姓……」这番话说出口,他自己都觉得苍白无力。
华筝发出一声几不可闻的冷笑,目光如刀:「大宋腐朽,那我大元如何?」
吕文德脸色煞白如纸,嘴唇颤抖,汗水滴落得更快。他想起伯颜那笑里藏刀
的脸,兀良那颐指气使的姿态,蒙古兵挥向平民的屠刀,城中汉人那低眉顺眼的
死寂眼神……他张了张嘴,喉咙里滚动着「残暴」二字,却终于被恐惧扼住,失
去了所有勇气:
「臣乃新降之人,不敢妄议大元……」
华筝起身,缓步近前,声音如冰刃划过他的耳畔:「我大元的毛病,我自知
晓。金刀驸马若无挂念,怎会弃草原驸马之荣,千里来守这襄阳?儒家汉制,懦
弱如羔羊,待宰而已;长生天的勇士,杀戮成性,贪婪如豺狼。可这世间,不该
只有羔羊与豺狼,人,也不该如此。」
她从袖中取出一本薄薄的经卷,封皮暗红,隐隐有火焰纹路,递到吕文德颤
抖的手中:「这《明尊经》,你若痛苦迷茫,便翻来读读。或有明路。」
吕文德捧着书,双手发颤,指节因用力而泛白。他抬头看向华筝,眼中满是
惊惶、困惑,还有一丝被看穿后的绝望。
华筝的目光深邃如夜空中的星火,声音低得像是贴着他的耳朵在呼吸:「汉
水之畔、襄阳和鄂州的汉人,三十几万生灵,不再是羔羊,也无需再向豺狼乞活。
他们需有人为他们指一条路。你若愿意,有人自会引你——引他们。」
她转身拍了拍手,不再多言,衣袂掠过烛火,影影绰绰。阳破天推门而入,
恭送吕文德离去。夜风卷着他失魂落魄的背影,消失在长廊尽头。
吕文德回到偏院,像一尊石像跪坐灯下,久久无语。烛火跳动,映得那经卷
上的火焰纹路如活物般蠕动。他低头,用颤抖的手翻开书页,第一行字跃入眼帘:
「明神在上,照我前路。」
他指尖一颤,一滴滚烫的泪水砸在纸上,洇开一团浓重的墨痕。窗外夜色如
墨,风声如泣,他捧着这本薄薄的书,像捧着天下唯一的火种,胸中剧烈起伏,
久久不能平静。
次日清晨,襄阳北门再度大开。华筝一袭银狐裘袍,腰束玉带,胯下白马如
雪。她身后百余骑护卫,旌旗猎猎,阳破天紧随其侧。
她回望城头一眼,目光掠过那面「元」字大旗,终究未发一言。马蹄踏碎晨
霜,一行人渐行渐远,尘土掩去了背影。
吕文德立于城门洞下,双手笼在袖中,怔怔望着那抹白影没入官道尽头。风
卷残旗,吹得他鬓发微乱,心头却空落落的,像被挖去一块。华筝昨夜那句「有
人自会引你」,犹在耳畔回响,可他仍不知该信几分,又该怕几分。
「吕大人。」身后忽响起生硬的汉音,带着年轻人的傲慢。
吕文德回身,只见兀良大步而来。少年将军一身玄色软甲,腰悬短刀,嘴角
噙着惯常的轻蔑。两名亲兵提着灯笼,随行的竟还有慕容杰——灰袍飘飘,手按
腰间软剑,神情淡漠。
「地牢里的宋军降将、丐帮余孽,一个个嘴硬得很。」兀良冷笑道,「大汗
有令,降者免死,不降者……哼。吕大人,你是旧日襄阳守将,总该陪我走一趟,
省得他们说我们蒙古人不懂『仁义』。」
吕文德喉头一紧,只得拱手:「末将遵命。」
地牢位于太守府后,阴湿逼人。火把照亮铁栅,映出一张张憔悴面孔:有断
臂老卒,有血迹斑斑的丐帮弟子,还有几位昔日同僚——他们衣衫褴褛,却仍挺
直脊梁,目光如炬。
兀良踱步而行,靴跟敲得石板咚咚作响。「都不愿降?」他嗤笑,「杀了便
是,省得浪费粮食。」
吕文德心头一颤,忙道:「将军,这些人……好歹是本地子弟,杀之可惜。
或可再劝——」
「劝?」兀良斜睨他,「吕大人,你心软得紧。来人,一个个压回去,不肯
招供情报的,午时斩首!」
亲兵应诺,拖拽声、铁链声顿时大作。牢中有人破口大骂「鞑子」,有人低
声啜泣。吕文德双拳紧握,指甲掐进掌心,却终究不敢再言。
兀良忽然停步,眯眼问:「那金刀驸马的徒弟武敦儒和他妻子在哪?」
吕文德咽了口唾沫:「地牢狭窄,不够安置,已……已囚在隔间。」
兀良挑眉,眼中闪过一丝玩味:「哦?你对敌人倒体贴。带上来。」
片刻后,武敦儒与耶律燕被推入临时审讯的偏厅。两人皆以铁链锁肩,衣衫
虽破,却难掩昔日风采。
武敦儒眉宇间犹带郭氏弟子的刚正,耶律燕则高挑修长,比武敦儒还高出一
头,腰肢丰盈,胸脯起伏,即便狼狈,仍有种胡族女儿的英气。
兀良的目光在耶律燕身上定住,少年喉结微动。那双眼睛亮得吓人,像狼盯
上了羊羔。
他平日仗着伯颜是自己叔父,最喜掳掠良家,调教倔强女子,却第一次看到
如此高挑英武的身子,这种高大与丰满的极致结合,让他食指大动,心底涌起一
股阴暗而狰狞的征服欲——一种小马拉大车的征服欲,他要这高挑丰满的侠女,
跪在自己脚下,哭着求饶,求他操弄,甘为玩物。
这欲望的根源,要追溯到他年幼时某个午后。那年他不过十岁,草原上的风
正烈,吹得毡帐外的马匹嘶鸣不休。他本是偷偷溜回叔父伯颜的王帐,想讨些糖
果解馋,却在门帘缝隙处僵住身子,像被无形的铁链锁住了脚踝。
帐内羊毛地毯上,叔父伯颜那魁梧如熊的身躯正压着一个女人——不,不是
一般的女人,是他的母亲。
平日里高傲得像草原上最桀骜的母狼,此刻却赤条条地跪伏在地毯上,像一
条发情的母狗般撅起那对雪白丰满的肥臀。
高高翘起的臀丘圆润得惊人,臀肉厚实而弹性十足,随着伯颜的动作剧烈颤
动,荡起层层肉浪。母亲的腰肢本就修长有力,却在叔父的粗手中被死死掐住,
迫使她上身贴地,脸颊摩擦着粗糙的地毯,乌黑的长发散乱如瀑,遮不住那张平
日威严如今却扭曲得近乎淫荡的脸庞。
伯颜跪在她身后,裤子褪到膝弯,那根蒙古汉子特有的粗长阳具——青筋暴
绽、龟头紫红如拳——正一下下凶狠地捅入母亲的蜜穴。
插入的瞬间,母亲的臀肉被撞得向两边分开,露出那粉嫩的菊蕾和被撑得变
形、泛着水光的肉唇。阳具拔出时,带出一缕缕晶莹的淫液,拉成丝线,滴落在
地毯上;再猛地顶入,龟头直撞花心,发出「啪啪」的湿响和肉体撞击的闷声。
母亲的那处神秘的地方,那是他出生他的地方,他就是从那个神秘的地方被
生养出来,这个神秘之处被他看的一清二楚,这也是他第一次知道蜜穴是什么,
长什么样。
童年想象中母亲的蜜穴本是紧窄的,却在叔父的抽插下被撑得红肿外翻,穴
口四周的嫩肉翻卷着,像是被征服的战场,沾满白浊的战浆。
「啊……伯颜……轻些……你这畜生……」母亲的声音本该是怒吼,却化作
断断续续的娇喘和呜咽。她试图挣扎,双手抓挠地毯,指甲抠出道道痕迹,可伯
颜只是大笑,一手揪住她的长发往后拽,迫使她仰起头,露出修长的脖颈;另一
手则重重拍在她臀丘上,留下五道红印,臀肉抖动得更剧烈。
「嫂嫂,叫大声些!我是不是比兄长插的你更爽!」伯颜低吼,腰杆如打桩
机般狂顶,每一下都顶到最深,阳具根部撞上母亲的臀缝,发出沉闷的「啪」声。
母亲的脸上,痛苦与快感交织成一种诡异的痴迷。她咬着唇,试图压抑,却
终究忍不住张开嘴,发出高亢的浪叫:「嗯……啊……要死了……伯颜……你比
他插的爽……」
她的身体背叛了意志,那对硕大的乳房垂吊在地毯上,随着撞击前后甩动,
乳头硬挺如樱桃,摩擦得地毯湿了一片。汗水从她高挑的脊背滑下,汇入臀沟,
再被阳具带出,混着淫液溅得到处都是。
她的臀部本是那么骄傲的弧线,如今却像献祭般高撅,迎接叔父一次次野蛮
的侵入,穴内层层褶皱被阳具碾平,又在拔出时贪婪地吮吸,仿佛舍不得那根征
服者的肉棒离开。
兀良躲在门帘后,小小的身子颤抖不止。他本该冲进去哭喊,可一种陌生的
热流从下腹升起,让他双腿发软。
那一刻,他看见母亲——那个能单手拎起羊羔、目光如刀的女人——在叔父
身下彻底崩塌,化作一滩春水。她的快乐不是伪装的,那种从骨子里涌出的颤栗、
那种从灵魂中对父亲的背叛,那被填满后的满足,让他这个偷窥的孩子第一次感
受到权力的真谛:征服高大的女人,让她们在自己胯下如狗般乞怜。
从那天起,这画面如魔咒般烙在他心底。母亲背叛父亲的影子成了他所有欲
望的模板:高挑、丰满、倔强,却最终屈服。
那些被他掳来的女子,他总试图重现那场景——让她们跪伏、撅臀、浪叫,
可她们要么太娇小,要么太顺从,从未真正触及他内心的空洞。
直到看见耶律燕。那女人身高近五尺八寸,骨架匀称,胸脯饱满得衣衫欲裂,
腰肢收紧,臀线圆润挺翘,带着胡族野性的力量感。她的影子与母亲重合得惊人:
同样高大,同样英武,同样有一股不屈的傲气。
兀良想象着将她按在地毯上,像叔父对待母亲那样,背叛了自己的夫君,撕
开她的衣衫,掰开她修长的双腿,看着那丰满的臀丘在自己阳具下颤抖、开花,
穴口被撑得红肿,淫液四溅。她会挣扎,会咒骂,可最终会像母亲一样,发出那
种混杂痛苦与痴迷的呻吟,彻底臣服。
这不是爱欲,而是扭曲的仇恨与自卑。他恨伯颜抢走了父亲的财产、母亲的
威严、培育过自己作为卵子的子宫,把自己生出来的通过的那条专属的阴道,却
又羡慕那征服的快感。
他要证明自己比叔父更强,通过耶律燕——这个比母亲更完美的猎物——来
填补童年的裂痕。让她哭泣、求饶、撅起屁股如狗般迎接他的阳具,那时,他才
能真正成为草原上的狼王,而不是伯颜脚下的影子。
伯颜对他颇为看重,他心下了然,但每次心里都隐隐作痛——莫非自己是伯
颜的种?而不是对他恩重如山的父亲!
武敦儒看他贪婪的、几乎要将妻子生吞活剥的目光,不由得怒骂:「鞑子小
儿,有种冲我来!」
兀良充耳不闻,缓步逼近耶律燕,比了比身高,自己的头才到她的双唇处。
这身高差非但没有让他退缩,反而更刺激了他的兽性。他忍不住伸手挑起她下颌。
耶律燕猛地一甩,力气奇大,险些挣开铁链。兀良却笑得更欢:「哟,野马劲儿。
放心,我不急。」
他手指下滑,隔着破损的衣襟,肆意抚过她饱满的胸脯,又探向那不堪一握
的纤腰与挺翘的臀线。耶律燕羞愤欲死,拼力挣扎,铁链哗啦作响,口中骂声不
绝。
那挣扎非但没有激起兀良的半分怜悯,反而让他脸上的笑容愈发狰狞,享受
着这猎物临死前的反扑。
兀良低笑,声音里满是病态的快感:「再动,我就剁了你夫君一根手指,如
何?」
耶律燕浑身一僵,泪水在眼眶打转,似断了线的珍珠,却终究垂下头,任那
只手继续亵玩。武敦儒目眦欲裂,嘶吼着扑来,却被亲兵死死按倒,脸颊在粗糙
的石地上摩擦,发出痛苦的闷哼。
吕文德再也看不下去,胸口仿佛被巨石堵住,他踏前一步,声音都走了调:
「将军!她……她是女流——」
「女流?」兀良终于将目光从耶律燕身上移开,转向他,眼珠一转,笑得阴
鸷如鸮,「吕大人,我可没用刑,也没强迫。我只是问话。」
他转向慕容杰,语气变得轻佻而理所当然,「慕容先生,你那点穴功夫,能
让这娘们儿使不出半分力气?」
慕容杰淡淡一笑,似对女色浑不在意,眼中只有对武学的痴迷:「自然。姑
苏慕容,点穴天下第一。七日内她就和常人无异。」话音未落,他指尖如电,连
点耶律燕数处大穴。耶律燕只觉四肢百骸瞬间一麻,一股酸软感席卷全身,顿时
软倒在地,再无半分内力,像一尊被抽去骨架的精美雕像。
兀良满意地拍手,俯身在耶律燕耳畔,用只有两人能听到的声音低语:「我
听吕大人的,不强迫你。但你若自己送上门来……可别怪我把你夫君的十根手指,
一根根喂狗。」他直起身,冲亲兵一摆手,「带走,好生『伺候』。」
吕文德又惊又怒:「华筝殿下已有懿旨,不得害他二人性命!」
兀良冷下脸色,一字一句道:「我可没说要她的命!我一没动刑,二没逼供,
只是单独问话。吕大人,你管得未免太宽——你如今,不过一介后勤都督!」
「后勤都督」四个字,像四根钢针,狠狠扎进吕文德的心里。他僵在原地,
眼睁睁看着耶律燕被两个亲兵像拖拽一件货物般拖走。她被拖走时,奋力回眸望
向夫君,那眼神,从绝望变成死寂,像一滩再也无法燃起的血。
「不——!」武敦儒发出野兽般的嘶吼,用尽浑身力气撞向铁栏,额头血流
如注,顺着他年轻而刚毅的脸庞蜿蜒而下,触目惊心。
慕容杰负手而立,目光只在耶律燕被点中的穴位处流连片刻,便已移开,仿
佛刚才只是完成了一次精准的解剖实验。
兀良则哼着草原上的小曲,嘴角勾起,脑中已浮现那高挑丰满的身躯在自己
身下颤抖、屈服的模样——他要慢慢折磨,慢慢调教,直至她心甘情愿,将他视
为主人,甘为性奴。
地牢火把噼啪作响,照得众人影子扭曲如鬼魅,在墙壁上疯狂舞动。吕文德
踉跄后退,胸口堵得发慌,仿佛肺里灌满了这地牢里腐烂的空气。他靠在冰冷的
墙壁上,指节无意识地死死抠着墙缝,指甲崩裂也浑然不觉。
他落寞地走出地牢,清晨的阳光刺眼,却没有半分暖意。他像一个游魂,回
到那方偏院,瘫倒在廊下。
这里,曾经是他府邸的一部分,如今却成了他的囚笼。世界变了,只是变得
太快,快得让他来不及死,只能苟活。
他闭上眼,武敦儒额头流下的血,和耶律燕那死寂的眼神,在他脑中反复交
替。那不是将士的死,那是羔羊在被豺狼分食前,最后的哀鸣。而他就是那个打
开羊圈的人。
悔恨、无力、屈辱……像无数只噬心之虫,啃得他千疮百孔。他猛地想起昨
夜华筝递来的那本经卷,颤抖着手从怀中掏出。
封皮暗红,火焰纹路在阳光下若隐若现,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又像一抹不灭
的星火。他翻开书页,那「明神在上,照我前路」八个字,仿佛带着一种奇异的
魔力。
「照我前路……」他喃喃自语,眼中一片迷茫,「我的路在哪?在这豺狼遍
地的地狱里,哪有路?」
他想把书扔掉,想撕碎这虚假的希望。可手指一接触到那温热的书页,却又
舍不得。这是他唯一的慰藉,也是他唯一的毒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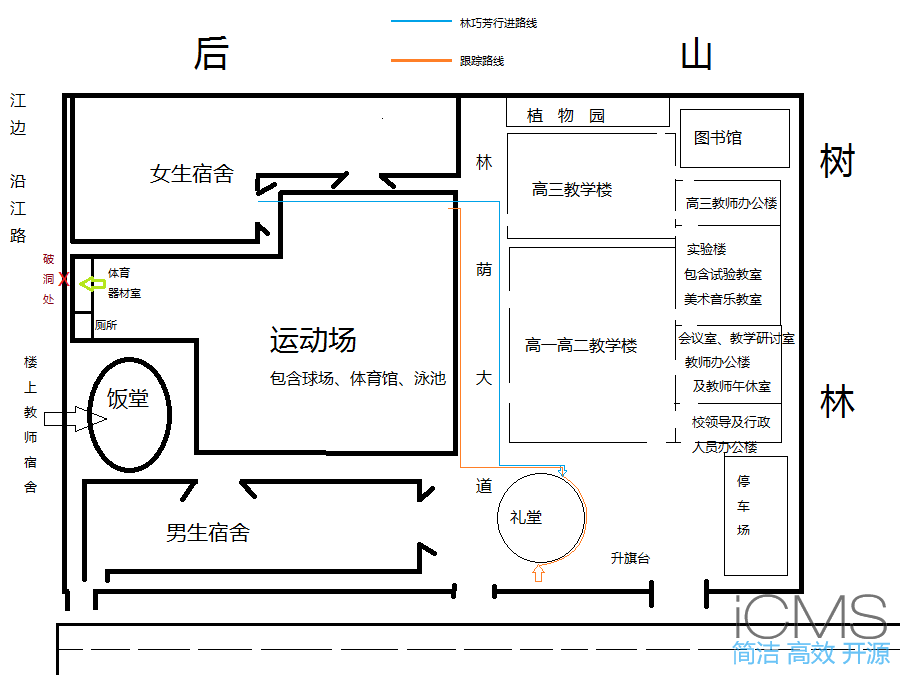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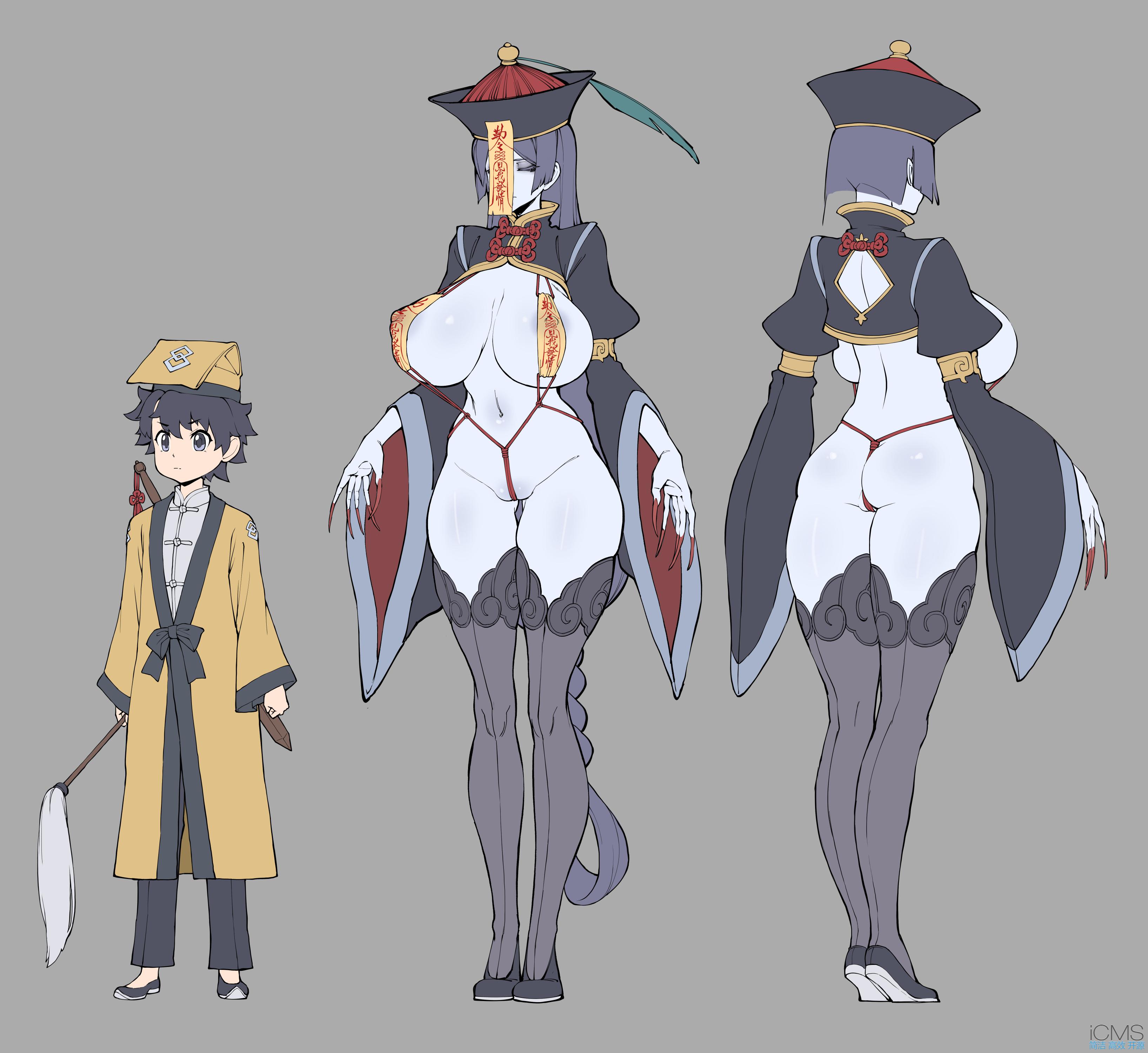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